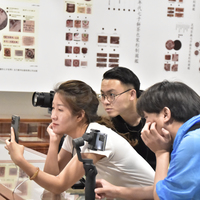有消息称,香港近日刚刚落幕的某拍卖会上,有史以来最贵的茶以2632万港元落槌,相当于2317万人民币。
2632万港元,“一锤定音”的回响震惊四座。茶界立马投去歆羡的目光,仿佛剧场之上,一幕意想之外的剧情横现,列座仪态万方。
据说在市场上,藏家碰到1920年福元昌号简茶的概率只有宋聘号的1/5,十分珍稀。2632万港元(2317万人民币)/件的百年福元昌号普洱茶,单价超过331万人民币/饼,可能又一次刷新了历史记录。
1920 年 紫票 福元昌號
数量 : 1 筒
重量 : 2236g
工序 : 生茶
成交价:26,320,000港币
23,170,000人民币
拍卖会成交的所谓有史以来最贵的茶
1920年,五四运动刚刚落幕,直皖战争爆发,以李大钊为核心的北京第一个社会主义小组成立,陈独秀主持起草《中国共产党宣言》,至今已近100年。
100年,我们不断在挑战着对食品的认知极限。其实说来奇怪,在所谓“越陈越香”的语境下,具有相同属性的白酒、红酒、陈醋、火腿等食品的炒作就很难出现这种100年岁月的跨度。即便酒类企业的规模乃至其基酒和产品的存储更规范,并且最早建立体系。但是这些年,我们什么时候听到茅台、五粮液这样的企业把陈放100年的老酒搬出来说事了呢?
给你个500年前的猪蹄,你敢吃吗?
福元昌原本是一个被历史遗忘了的茶商字号,这些年随着老茶的炒作,特别是针对福元昌的一些老茶炒作,导致这个已经湮灭的老字号又通过各种方式借尸还魂。“福元昌”这3个字注册很困难了,于是商家加个前缀,市场上就出现了各种福元昌。大家也会借着这个热点,站出来向公众表白自己与福元昌的渊源。
但事实上,我们现在谁也说不清,100年前,究竟哪位高人能够做到。从千里迢迢的香港赶来,穿越军阀及土匪混战的各个势力区,最后来到了云南茶山,然后装着这些茶品又原路返回。抵达香港之后,这些都舍不得喝,非要预言式的留下来,并且保存至今。这些历史细节可能我们市场上的各类福元昌都说不清楚,但他们还是敢大声向公众说,他们手上有那个100年前“网红高价茶”的精准配方。
1920年,中国五四运动才结束不久,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才成立的,这饼茶比党还要年长一岁,跨越了风起云涌的近代史。它如果一直沉寂在香港的某个仓库里,那它有可能不知道,轰轰烈烈的北伐正隔着江河在大陆展开,之后国共破裂,10年内战,然后抗战爆发,日本人还占领了香港。这片茶的主人一直安然无恙?放置茶的仓库没有在炮火下损伤?或者说在逃难与生死线上挣扎之际,依然给这茶提供了近乎完美的保护措施?
栩栩如新的笋壳、竹篾、茶虫饼面在考诸位的智商
很难想象,我们拆开拍卖现场的那一提茶,笋壳崭新如初。更有甚者,有些收藏者可能还高薪聘请了一位穿越者,带着100年后才有的电脑激光技术,在同样是1920年的福元昌茶的笋壳包装上留下了印记。据说,笋壳新是这款茶采用了真空包装,看来一位穿越者还干不完这活,得是一个茶叶包装团队带着设备集体穿越才出现得了这个效果。
所以也难怪要拍卖出个天价,主要是那个包装团队的“穿越路费”贵啊!
如此博学多识的茶精,是该作为佐证历史的文物收藏品?还是该作为保健养生的神级饮品?100年的普洱茶,究竟能不能喝,好不好喝,有没有品饮价值?我们一无所知。
如果是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清代光绪年间“普洱金瓜贡茶”一样的文物藏品,以上的问题就可以忽略,它的价值也不该以饮用茶来衡量。
然而问题之在于,这些茶给社会的普遍认知是用来品饮的,但如果没人舍得喝,没人喝过,或者说有人喝过了,但喝的却是一些商家明目张胆造假的替代品,这些茶是好茶的定论和宣传,缘何而来?
如果非得用饮用价值来冠名,我认为这东西肯定不能喝,所谓“神倦败味而木也”。诚如热爱普洱茶金德庆师弟所述:
“我浅薄的经验告诉我:五六年的茶存放好喝起来很舒服,香气、韵味、转化都很好;十多年的茶喝起来体感最舒服,茶的香气经过存放淡了,但韵味更足,喝了浑身通透。”
那么,究竟是谁,在主导这场拍卖,谁是最终的得力者?香港拍卖会上年年有之,一次比一次更加稀奇、昂贵、陈年的普洱茶从何而来?
其实,普洱茶界这样的妖异事件,每年重复来多次,以达到教化和宣传的目的,让不明白的人来买这天价普洱茶收藏发财。
细探才知,原来除了百年福元昌号普洱茶以外,鼎鼎大名的“大红印”也是这次拍卖会的主演。
鼎鼎大名的“大红印”
“大红印”我们并不陌生,它一出场就像似一个提线木偶,我们直接就能联想到站在背后操控提线的白水清先生。很多非普洱茶圈人认识白水清先生是通过文化大师余秋雨先生的《极端之美》,此前这位文化大师在茶界没有发过声,但毕竟是个掌握了文化话语权的大师。经过他的妙笔,把普洱茶写得让人魂牵梦绕。唯一不足的地方,就是最近重读大作,发现先生提到的很多懂普洱茶的高人要么锒铛入狱,要么被拉下了神坛。
在锒铛入狱的角色里,最引人瞩目的应该就是那位副省级官员沈培平先生。一个政府官员,一个文化大师,再加上白水清这样的普洱茶大师,三个站在制高点上的灵魂重叠在一起,将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“大红印”,余、白二人以这位懂普洱茶的副省级干部为荣,四处炫耀,引为谈资。但天网恢恢,在反腐的铁拳之下,这位识得“大红印”的伯乐因贪腐而入狱十二年。
至此,江湖上有笑传:宝剑赠英雄,红印配贪官。
相比“香港某拍卖会”上幕后玩家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戏路,余秋雨先生在《品鉴普洱茶——普洱茶大排序》中的演技就更胜一筹了,他谈到与沈培平先生的相识时,言是不期而遇,转角之爱。他说:“那天我在飞机上正好与他邻座,就聊了起来。”由此展开他向沈大师“问道”的演绎之路。
最终,这些人,有的因“红印”走上了爆发横财的循环炒作之路,有的在一发不可收拾的贪念中入狱为营,还有的以文采话茶,佯装谦谦君子,说完《君子之道》,又谈《极端之美》,在装逼的文化苦旅上渐行渐远。
那么,“大红印”究竟是何来头?
邓时海先生编著的《普洱茶》一书,其中的第五篇《茶谱篇》,他概述了红印圆茶的来源与流通,认为“大红印”是“现代普洱贡茶”,并梳通说:
“1949年佛海茶厂,改名为勐海茶厂,第一位厂长唐庆阳先生亲口说:‘打从范和钧时期开始,那种红色茶字的普洱园茶,一直都是选用勐腊最好茶菁做的,而在勐海一带产的茶菁是做成绿色茶字的普洱园茶。’勐腊县包括勐腊镇、易武镇等,所以红印的茶菁是来自易武茶山大叶种茶树,那里的普洱茶菁,一直都被定为最优良的。”(注释:唐庆阳先生退休前一年担任过勐海茶厂的厂长)
邓时海认为“大红印”茶菁原料来自易武茶山大叶种茶树。事实上,并没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证邓时海先生此观点,他的“定论”仅是对于唐庆阳先生:“打从范和钧时期开始,那种红色茶字的普洱园茶,一直都是选用勐腊最好茶菁做的”一句的过度发挥和主观臆断而已。
干仓储存的"福元昌号"
邓时海先生想著普洱茶学之书,立普洱茶学之说的热切与初衷,就像他对普洱茶学的贡献一样,不可小觑。但邓先生如此撰作、编造、臆断的部分恐会贻误后学,为投机倒把者提供可乘之机。
因为,上世纪40、50年代,易武镇优质茶菁区域交通堵塞,根本无法集中收购足量的茶菁去制作批量茶产品,刮风寨、麻黑等地山高路远,道阻且右,所谓“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”,“黄鹤之飞尚不得过,猿猱欲度愁攀援。”
茶商收购易武茶农足量的茶菁原料,送到勐海制作批量“红印”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
而恰恰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,成为读者迷信源头的同时,也成为了所谓普洱茶“大师”白水清等人的炒作契机和手段,以及沈培平、余秋雨等人包装“身份”的依靠。
当然,我们那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号称是要重塑普洱茶的语法,但我们细细品咂他笔下的语法,也不过是把邓时海的臆想换了一种表达。运笔于书闺之内,大刀阔斧、阔论品鉴普洱茶,一二三十五六七......,令人佩服。
同时,先生们不约而同的搬出邓时海先生前后期红印园饼的分期,认为:
“红印普洱茶是1949年开始运销到香港。红印普洱茶可分为‘早期红印’茶饼和‘后期红印’茶饼,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产品。”
对此,邓时海先生还提出,红印茶饼前后期包装印刷,及字体线条变化缘由等诸问题的分析,看似天衣无缝,其实,这些说法都是有待商榷的。
有确切史料记载,中茶商标注册于1951年。按照邓先生的分期,要说在1951年以前四十年代,就有“红印”中茶商标,如此不分轻重的言论,纯属无稽之谈。
“大红印”究竟已成历史,或是缥缈虚无的存在,我们无法确切,传说中的“大红印”有没有真实存在。因为拍卖会上以天价交易的红印,存在着诸多疑点。
仓储问题也是“红印”的一大疑问,邓时海先生在初版于2004年的《普洱茶》一书中提出,“红印”茶饼都是“干仓”贮藏,前期约为65年,后期约为55年,算而今天,“大红印”前后期茶饼已有70年和80年的历史。
70至80年的骨灰级藏品,与福元昌号1920年陈茶都有同样的问题。姑且不说这款“老茶”能不能饮用,有没有毒的问题。
从近日香港某拍卖会上出现的天价“干仓”红印来看,“干仓”所引出的疑问层出不穷。
素闻香港为“潮仓”地区,流于香港70至80年的“大红印”,何来“干仓”之说?拍卖会的“干仓”“红印”如何在香港存为干仓?或者保存者如何烘为“干仓”?干仓之谜是这场拍卖会的最大漏洞,谜底不攻自破。
余秋雨先生多次盛赞沈培平先生的管理学问及普洱茶学问,把沈先生、白水清先生归为不喝“下等茶”的大师,列为自己的同道中人。这些年,不知余先生是否还喜于在朋友跟前提起与沈培平先生的友谊,和茶会故事?
给你个1200年前的“火腿”你敢吃吗?
给你个1200年前的“火腿”你敢吃吗?我很难想象秋雨先生在《极端之美》中对那些古董茶啧啧称赞的感受了。这倒也是一种极端,挑战着我们的极端心理耐受能力!
沈培平先生对云南普洱茶产业的发展可能做过一些推动性的贡献,但很难说功过相抵。这就像:再有才华的诗人,倘若他杀人嗜血,再高的才情也改变不了他是杀人犯的命运。
从2004年到2013年,再到今天,普洱茶市场变态、恶性的市场竞争,又何尝不是沈培平先生一手主导埋下的祸根?而沈、余诸人的共同至交白水清,就是其中的每每坐收渔翁之利的,这恐怕是人尽皆知的。
我们知道,包装自己是某类“文化人”的特长,话茶时总要拉上金庸、白先勇等大先生,对普洱茶之学亦是如此。
余秋雨曾对普洱茶进行过一次所谓的大排序,提出要冒天下人之不敢为,对各类普洱茶名品排名排序,然后再向他口中的“大师”、“老朋友”白水清、沈培平、何作如、太俊林、张奇明、王家平们求证,寻找不谋而合的契机,真是良苦用心。
他的品鉴普洱茶,将“宋聘、福元昌、向质卿、双狮同庆、陈云号”五大“号级茶”排为前五名;将“大红印、甲乙级蓝印、红印铁、无纸红印、蓝印铁饼”五种“七子饼”分别列为前五名;将“八八青饼、七子黄印、七五七二、雪印青饼、八五八二”五类“印级茶”排在前五名。
讲的一套接一套,像是这些天价茶都在他们这一伙人的手中,时刻品类把玩似的。
尽管余先生最后总结说:“可见,在口味等级上,(我与)高手们分歧不多。这样,我也就放心了。”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,余先生之观点,更多的是与沈培平的分级观点相重合的。
据说“大红印”原料来自易武茶山
是不谋而合,还是座谈同谋?恐怕只有坐在一起喝“大红印”的人才心知肚明。
相对于现在诸多身体力行,亲力亲为,行走茶山的普洱茶学者喝普洱茶爱好者来说。余秋雨先生对谈茶、品茶有自己独特的见地。
他习惯以文笔、文采喝茶,天马行空的想象和造作,用妙语连珠,缔造一系列根本不存在的虚假体验,令观众神魂颠倒,追捧不止。信而饮之,坑坑洼洼。
余秋雨先生试图建立一种有等级的茶话世界,推崇以白水清、沈培平等“普洱茶大师”,并将与之对应的“宋聘”、“大红印”“八八青饼”等所谓的高档茶与普通茶划清界限,进而图谋建立一种“有等级”的喝茶制度和茶的日常生活。
在我看来,阐明“上等人喝高档茶”的道理,就是余秋雨先生的品鉴普洱茶的核心思想。
然而,白水清逐渐走上了“传销式”的普洱茶“大师”之路,他所谓自己手中价值连城、一泡难求的“大红印”、“八八青饼”究竟是真是假,我们无从知晓?
沈培平早已成为囚笼困兽,再多、再贵、再高档的“大红印”对他而言也不过是贪欲的睚眦,或者他也做过抱着“大红印”闪闪发光,成为“大师”和“教皇”的梦,但他们都走向或终将走向穷途末路。
直到今天,余秋雨先生不知是否还在枯坐闺中,冥思苦想哪一种普洱茶是一等品的问题呢?李白说:“大块假我以文章”。李白又说: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”。
在我看来,香港近日刚刚落幕的某拍卖会,也是这伙人集中自编自导自演自炒起来的。
自编自导自演自炒的“高端茶”
我们今天所见的“大红印”,本质就是一种商业意义上的伪装,不过是后来才换上的做旧的假包装。而“大红印”的存在,亦只是白水清“普洱茶教父”与“营销家”的一种想象之物。
是时,民智已逐渐被文明所唤醒。时代越来越多的需要生活与品质,越来越多的需要回归日常,普洱茶的命运也摆脱不了这个趋势。
因此,在普洱茶是什么的问题上,我一直推崇古人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的观点,普洱茶存在的基本意义和终极目的,都是茶本身的饮品属性。陈年与否,古老与否,并不应该是衡量普洱茶优劣的主流标准。
茶是用来喝的,好喝才是硬道理。我们不能因为这株茶树古老、珍贵而昧着良心说好喝,也不能因为一株生态小树茶因为它小而无视它的饮用价值。
好茶在于生态、在于工艺、在于是否与生活对称,在于是否真心好喝、能喝,健康的、生态的、好喝的,就是好茶。
我相信,在未来,真正的普洱茶世界,只属于那些用心做茶,用心喝茶,平恒勤俭,上善若水的茶人。
(来源:石一龙)